金庸笔下的侠女,真的只为爱情存在?
人们依然怀念金庸,也怀念他笔下的江湖。
金庸写过脍炙人口的侠士,也塑造了众多出彩的侠女。不少人批评他小说中的女性多作为男性的伴侣存在,是男性角色和男性观众的欲望客体。诚然,金庸小说并非以女性为主体的书写。由男性作家塑造的侠女处于被表达、被观看的位置。男性武侠中的女性几乎都将爱情置于上位。她们为情所喜,也为情所困。但不容否认,金庸小说中的侠女确实是那个时代的亮色。她们一改过往女性受压抑的悲情形象,展现出磊落率真的风貌。
中国文化中有很多关于男性侠客的想象,比如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浮沉随浪,潇洒豪迈。但对于侠女则少有严苛的道德要求。这一对比在金庸武侠中同样有所体现。与担纲了太多伦理价值的英雄豪杰不同,侠女们的形象更加舒展自然。她们得以摆脱传统的家庭束缚,又不必成为公共领域的道德标杆。与今天流行文化中千篇一律的“大女主”相比,金庸笔下的侠女反倒个性鲜明,不拘礼法,有着别样的光芒。今天的文章带我们回顾这些生动活泼的侠女形象。
侠女,恣越于江湖与世俗之间
中国传统的侠女形象可追溯至唐传奇中的《红线》《聂隐娘》等作品,而后是明初的《水浒传》、晚清的《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等。
唐传奇重写意而轻细节,作者并不细致描摹侠女的性别特质,而突出其超人的神异身体。侠女仗义行事,并不依附于男性。她们被免除了家庭责任,但同时被赋予了庙堂的忠君伦理和江湖的隐逸气质。唐人裴铏如此描绘聂隐娘:本领高强,“白日刺其人于都市,人莫能见”。她与丈夫曾为魏帅左右吏,奉命刺杀陈许节度使刘昌裔,被其气度折服,转而投靠。隐娘两次以神力化解行刺,得厚礼;最终在刘昌裔调任京师后归隐山林。
晚清小说中的侠女则显现出更平民化的特征,杂糅了侠义英雄、闺房女子和贤妻良母的多重身份。其中较有代表的是《儿女英雄传》中的十三妹何玉凤。在小说的前半段中,何玉凤与豪杰交游,报得杀父之仇,还救下富家子弟安骥。而在故事后半段,何玉凤嫁给安骥,成为安家大奶奶,辅佐夫君,重振家业。
从侠女到贤妻的反差引发后世文人的批评。胡适曾评价何金凤在婚前是见解不俗的“超人”,婚后却跌落为劝夫考取功名的平庸女子。他将这种“堕落”归咎于作者的“迂陋”思想。但志向高远的侠女落入世俗,嫁为人妇,将江湖侠气转变为精明的治家才干,却也是侠女形象被平民文化吸纳的体现。
文学学者王昕如此分析何玉凤侠女身份的断裂:脱离了唐宋剑侠小说的神异身体,这位侠女就必须回归传统女性的性别角色,依靠家庭生活。小说以儒家“安身取誉”的人伦关怀为人物演变的线索。侠女的常人之身正凸显了近代文学的平民意识。
侠女形象也在中国电影史中大放异彩。女侠电影曾在1920年代末的上海风靡一时,而后在1931年国民政府对武侠神怪片的禁令之下逐渐消失。荧幕上的侠女通常女扮男装,武功过人,背负复仇使命。她们一改过往电影中悲情柔弱的女性面貌,展现出抗争精神和身体力量。
在《银幕艳史:都市文化与上海电影》一书中,电影学者张真指出,面对动荡的时局,“武侠神怪片提供了一次去往遥远空间的虚拟旅行,在这里人们重获自由、匡扶正义。”而众多女侠则突破了“传统女性受压抑的身体语言”,以恣越之态成为“戏剧张力和视觉奇观的中心”。
《女侠白玫瑰》《荒江女侠》等影片中的女主角多在复仇后走向婚姻,1929年由友联公司出品的《红侠》却与众不同。《红侠》的女主角芸姑在离家逃难时被掳走,幸得白猿老人相救且收为弟子。芸姑习得武艺后不仅手刃仇人,还救下另一名落难女子琼儿。在电影结尾,芸姑遵照师父的指示撮合表哥与琼儿成婚,自己却归隐峨眉。
芸姑并未落入嫁为人妇的窠臼,而是成为姐妹的拯救者和婚姻见证者,彰显出独立的侠义精神。她并未收获美满的爱情,却展现出洒脱的女性力量。这也是《红侠》的独特之处。学者周舒燕指出,芸姑从村女到女侠的转变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她的社会和性别身份,使她不再受家庭、婚姻的约束。因而她得以“从欲望客体的位置上逃逸,成为叙事的主体”。
金庸笔下同样可见众多个性鲜明的侠女。她们亦正亦邪,恣越于江湖与世俗之间。有批评者认为这些女性多作为男性的伴侣或倾慕者而存在,是男性角色和男性观众的欲望客体。诚然,与英雄义士结为眷属确实是金庸赋予女性的看似圆满的归宿。金庸小说并非以女性为主体的书写。侠女依然由男性作家塑造,处于被表达的位置。
金庸在作品集新序中言及,他希望借由小说传达爱护家国民族、和平互助、重视正义和是非等主旨。但如太过强调小说的教化功用,未免有人物服务于价值之嫌。这一点在英雄豪杰身上尤为明显。金庸笔下的男主角们大多担纲了安邦救国、扶贫济弱的伦理,形象多有刻板之处。
相比之下,女性角色则未被寄予如此厚望。在武侠江湖中,侠女们得以摆脱传统的家庭束缚,又不必成为公共领域的道德标杆。其言行举止更加自然,在情节的延展中显出光芒。
“恶女”,弧光中的幽微人心
金庸早期创作中的“恶女”大多因爱情而走火入魔,如为了与师兄相恋而被背叛师门的梅超风,被陆展元抛弃后开始滥杀无辜的李莫愁。在武侠世界中,男主角们面临家与国、情与义、生与死的抉择,而女性的踌躇似乎只关痴情。
这一问题在中后期的长篇小说里有所改观。侠女们开始面临更复杂的处境,她们在阴差阳错和个人决断中走向不同的命运分野。赵敏和周芷若便可如此对照而观。赵敏是汝阳王的女儿,自小衣食无忧,张扬而热烈;周芷若则是父母双亡的汉水渔女,前期柔弱仁懦,后期则阴毒狠辣。
很多人都赞扬坦率真挚的赵敏,而对患得患失、工于心计的周芷若颇有微词。但如果说赵代表了磊落坦荡的“超人”形象,周则更像是在良知和心魔之间摇摆的凡人。从她走入迷途而后知返的转变中可窥见善恶交织的幽微人心。
周芷若的变化始于成为峨眉派掌门之后。彼时她是派内最年轻的弟子,虽深得师父赏识,但武功和资历都难服众人。灭绝师太临终前逼她立下毒誓:接任本派掌门,利用张无忌的信任取得屠龙刀和倚天剑。
同为峨眉派高徒的纪晓芙也曾面临师父的威胁。在得知纪晓芙与杨逍的私情后,灭绝师太逼她杀死杨逍,之后便可继承掌门人的衣钵。但她拒不从命,甘愿赴死。与纯粹刚直的师姐不同,周芷若内心有太多顾虑和欲念。
她本性正直,从小对师父言听计从。当师命与道义、情感冲撞时,她最终走向阴影,用计谋骗得刀剑,伤害殷离,嫁祸赵敏。纪晓芙不蔓不枝,周芷若则在诸多选择前左支右绌。她既希望不违师命,又不愿辜负心爱之人;既向往爱情,又渴望权力。小说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张无忌道:“我才干不足以胜任教主,更不想当教主。何况我教上代教主留有遗训大戒,我教教众不得作官作府、为帝为皇,纵然驱除胡虏,明教也只能身处草野,护国保民,决不能自掌天下权柄。将来如天下太平,这一教之主,更非由一位英明智哲之士来担当不可。”
周芷若道:“明教上代当真有这样的规矩?如若将来的皇帝官府不好,难道明教又来杀官造反、重新干过?我瞧这条规矩是要改一改的。......我是峨嵋一派的掌门,肩头担子甚重。师父将这掌门人的铁指环授我之时,命我务当光大本门,就算你能隐居山林,我却没这福气呢。”
周芷若和张无忌都是被迫走上权力高位。然而张并不贪恋权力,只愿归隐山林;周则入世而现实,并不掩饰谋权的志向。两人心性的分歧可见一斑。
“深解义趣,涕泪悲泣”是《倚天屠龙记》的题眼,此语出自《金刚经》。金毛狮王谢逊一生杀人无数,遭周芷若暗算而被囚于少林寺中。他每日听得僧人诵念《金刚经》,终于彻悟。
欲念、悔过、解脱是这部小说的关键词。悔悟改过的除了谢逊之外,还有周芷若。在故事末尾有一处高光时刻:少林决斗前夜,周芷若拒绝了张无忌的援助。张无忌道:“咱们只须问心无愧,旁人言语,理他作甚?”周芷若答:“倘若我问心有愧呢?”“问心有愧”或许也是金庸给予周芷若的评语。从寄人篱下的渔家女到身负绝学的掌门人,从攻心设计再到计谋被揭穿,她想抓住太多东西,但最终皆为虚妄。
赵敏似乎永远明艳而果敢,在要紧关头总能做出无私的选择。从她的角度看,《倚天屠龙记》是个无甚新意的爱情故事。相比之下,周芷若身上则有很多旁逸斜出的晦暗部分,不圆满的结局中有欲望和道义的撕扯,有怯弱和心虚,有愧疚与和解。这些勉强不得的事与情正是人物的弧光所在。
侠女们真的只为爱情而存在吗?
江湖的一面是暴力,另一面则是柔情。爱情是武侠小说中不可或缺的线索。在“侠骨柔情”的基调里,男主角是故事的核心,围绕在他身边的女性往往不止一位。段誉、韦小宝、张无忌和杨过皆为此类。学者戴华萱指出,男性武侠世界中的女性将爱情置于上位,这是晚清才子佳人小说模式的延续,也是女侠屈居于附属客体位置的主要原因。
金庸小说中不乏拥有美满爱情的女性,如与郭靖长相厮守的黄蓉,以及虽然刁蛮却深得耶律齐宠爱的郭芙。但也有一些角色爱得很辛苦,甚至最终并未收获姻缘。在爱情之外,金庸于她们身上寄托了更广阔深邃的人生命题。
郭黄夫妇的次女郭襄便为一例。相比于母亲黄蓉,她的戏份并不多。金庸擅长用华丽词藻来描绘女性容颜。黄蓉是“肌肤胜雪、娇美无匹”;郭芙是“脸如白玉,颜若朝华”;但写到郭襄时只说她清雅秀丽。
金庸并不强调郭襄容貌出众,而更多着墨于她的性情,寥寥数笔就勾勒出其鲜活形象。如好友倪匡评价:“郭襄不是黄蓉,不是黄药师,她是她自己。”她所具备的是一种超越性别的侠勇之气。她仗义疏财,交友不问高低贫贱。在风陵渡口兴之所至就用金钗换酒,宴请众人;在少林寺看到觉远受人刁难就打抱不平,非要讨一个公道。
郭襄单恋杨过的故事常令读者惋惜。她初时心怀对神雕大侠的仰慕,与杨过相处数日,得知他与小龙女情深义重,徒添惘然惆怅。杨过曾许她三枚金针,以满足她三个心愿。郭襄的前两个愿望都与自己有关:一是希望看到杨过的真容;二是希望自己十六岁生日时他能来襄阳。第三个愿望则毫无私心,只要杨过不再寻短见。
如果仅仅将天涯思君之“思”理解为求而不得的相思之苦,未免将郭襄看得太过狭隘。郭襄最初对杨过只是依恋与崇拜,但随着她游历四方,这份情谊在阅历积淀中有了更厚重的意味。
郭襄的使命并不是成为男性的伴侣,而是找寻真我。她要超越父母的光环,也要超越她难以忘怀的神雕大侠。金庸小说中的女性掌门人并不多见,即便有也多以年长女尼的面目出现,如衡山派的定闲、峨眉派的灭绝师太。作者并不交代她们早年的经历。唯独对于郭襄,金庸描摹了她天真潇洒的少女时代。可见这一角色的分量。
另一位出场不多但颇有深意的侠女是任盈盈。她首次登场时,只闻其琴萧之声,不见其人。令狐冲误将她认作“婆婆”,她并不主动纠正。读者对她的印象大多来自旁人的言语——她是日月神教的圣姑,性情乖戾,行事残忍。直至全书将过半时她才现真容,之后又匆匆退场,隐却至群侠纷争的幕后。在《笑傲江湖》中金庸极力铺陈江湖险恶,对于内敛淡泊的任盈盈,却是点到为止。
任盈盈集合了很多看似矛盾的品质。她位高权重,手握杀生大权,却又厌恶争权夺利;她极有城府,周旋于三教九流之间,面对心仪之人时却又腼腆害羞。这些特质奇妙地在她身上并存,圆融盈满,恰如其名。金庸在小说后记中如此评价任盈盈:“她生命中只重视个人的自由和个性的舒展,唯一重要的只是爱情。”但或许她更看重的是自由,而非爱情。不仅是自己的自由,也有伴侣的自由。
令狐冲与小师妹岳灵珊的爱是浓烈的儿女情长,而他与任盈盈之间则更多是相敬如宾,理性克制。直至岳灵珊为丈夫所杀,令狐冲也无法放下痴情。这是任盈盈勉强不得的事,她知道“两情相悦,贵乎自然”。
冲盈之间不像普通情侣,而更像是在险恶丛林中结下生死之交的知己。纵观全书,爱情并不是《笑傲江湖》的主线。整部小说都充满了血雨腥风:渴望一统江湖者杀人如麻;觊觎《辟邪剑谱》者不惜走火入魔;想要金盆洗手者也只换得灭门之祸。如何在重重凶险之中生存下来,并且活得舒展自在才是这本书的主题。而充盈二人则是幸运的盟友。他们都是追求自由、爱惜名节的隐士,在确认了彼此的相似本性后决定相濡以沫。
金庸以工笔勾勒黄蓉、赵敏等人,细致入微;对于郭襄、任盈盈则更多是写意。两位角色都有太多留白,引人想象,也显出高远意境。黄蓉和赵敏都才智过人,但遇到郭靖、张无忌后,她们的人生任务只剩下辅佐夫君。
相比之下,任盈盈和郭襄却始终保有稳固的自我。爱情并非她们人生的全部,而是她们成长的方法。甚至可以说,她们爱的并不是具体的杨过和令狐冲,而是侠士所代表的精神——仁厚仗义、自由逍遥。这种价值也引领她们不断行向开阔之处。
名为武侠,实为世情
金庸写武侠小说是在写人性。他在新版作品序言中说:“塑造一些人物,描写他们在中国古代的、缺乏法治的、以武力来解决争端的不合理社会中的遭遇。当时的社会和现代社会已大不相同,人的性格和感情却没有多大变化。”此语道出他笔下的角色能引人共鸣的原因。
作家杨照在《不止江湖:用武侠想象另一种可能》中谈道:武侠世界充满虚构,充斥着不合理的情节,但武侠的核心价值却在虚构之外。
金庸作品名为武侠,实为世情。他前期的作品大多结局圆满,即便失败也悲壮豪迈,留得英名。郭靖成为一代大侠,与黄蓉终成眷属;两人在镇守襄阳时战死沙场,为后人称颂。这是黑白分明的童话。后期的作品则多了很多苦涩与无奈。曲洋与刘正风最终没能携手归隐,笑傲江湖曲成绝唱;萧峰误杀了一生挚爱阿朱,后来又因自觉背叛辽国而自刎谢罪。脱离武侠的残酷背景,这些离别、悔恨与误解或许也是世间常有的不如意事。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虚构中的刀光剑影远去,但古人的悲欢离合,至今仍映照在读者心中。这也是金庸武侠的长久动人之处。
-
 央视快评丨为促进文明传承发展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作出更大贡献 来源标题:央视快评丨为促进文明传承发展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作出更
央视快评丨为促进文明传承发展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作出更大贡献 来源标题:央视快评丨为促进文明传承发展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作出更 -
 今晚油价下调!加满一箱油将省5.5元 来源:央视财经 作者:平凡 孙永慧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新一
今晚油价下调!加满一箱油将省5.5元 来源:央视财经 作者:平凡 孙永慧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新一 -
2024重庆人工智能与先进计算发展大会举行 中新网重庆11月7日电 (梁钦卿)2024重庆人工智能与先进计算发展大会
-
 泰国参展商:参加进博会将共享中国大市场 期待实现互利共赢 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于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举办。进博会泰国参
泰国参展商:参加进博会将共享中国大市场 期待实现互利共赢 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于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举办。进博会泰国参 -
 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进入“冬眠” 中新网银川11月4日电 (记者 李佩珊)11月4日,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葡
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进入“冬眠” 中新网银川11月4日电 (记者 李佩珊)11月4日,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葡 -
 探寻西夏陵  位于宁夏银川的西夏陵位于贺兰山东麓,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
探寻西夏陵  位于宁夏银川的西夏陵位于贺兰山东麓,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
- 进博会:甘肃企业签约进口商品金额可观 深化合作、共谋发展。在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由我省679家企
- 秋来橘子红,食安记心中 转眼又到了炫橘子的季节,市场上各类品种的橘子陆续上市,引人垂涎
- 金庸笔下的侠女,真的只为爱情存在? 人们依然怀念金庸,也怀念他笔下的江湖。金庸写过脍炙人口的侠士,
- 读书遇上不合口味的翻译,就像吃鱼卡了刺 最近,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最新长篇小说《小城与不确定性的墙》中文
- 上个雪季我国冰雪旅游人数同比增长38% 收入同比增长50% 国新办6日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以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激发
- 庆阳:“数算电”融合,税务赋能新赛道 东数西算国家战略落地实施以来,庆阳市充分发挥能源资源富集优势,
- 黑龙江哈尔滨连续4年提高孤儿基本生活费标准 6日,记者从哈尔滨市民政局获悉,哈尔滨市集中养育孤儿基本生活费标
- 甘肃环县5万亩“苦柴胡”熬出甜日子 连续六年种植柴胡,甘肃省庆阳市环县虎洞镇高庙湾村铁匠塬组种植大
- 工信部:推动新技术与冰雪装备融合,助力冰雪运动蓬勃发展 国新办6日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
- 灵台:守护林草资源,绽放绿色希望 林草资源是陆地生态系统的核心支柱,是人类文明传承的绿色纽带,是
-
 金昌新先事 | 永昌2323户6850人住上安心房 永昌:2323户6850人住上安心房 2024年,永昌县严格按照优先将
金昌新先事 | 永昌2323户6850人住上安心房 永昌:2323户6850人住上安心房 2024年,永昌县严格按照优先将 - 长歌奋进,看国寿寿险75年跨越路 2024年是中国人寿成立75周年。从1949年到2024年,中国人寿始终把自
- 甘肃青少年的香港研学:知识与感悟之旅 11月3日至4日,由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甘肃省海外联谊会举办的陇原
- 从“靠天吃饭”到“数据吃饭” 浙江桐乡智慧农业显身手 地面智能机器人、无人机如何作用于农业园区?它们组成的管家搭子,如
- 临夏鲜切花:“绽放”国际市场 兰州海关6日发布消息称,今年前10个月,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69万枝、
-
 美联储下调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25个基点 11月7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在华盛顿出席记者会。美国联
美联储下调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25个基点 11月7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在华盛顿出席记者会。美国联 - 临泽县:“强工业”行动推动经济加速跑 今年以来,张掖市临泽县鲜明树立大抓工业、大干工业、大兴工业导向
- 透过数据看冰雪旅游热力十足 各地蓄势待发推动“冷资源”激活“热经济” 来源标题:透过数据看冰雪旅游热力十足 各地蓄势待发推动冷资源激
-
 新材料专区“首秀”助推低碳环保发展 进博会看未来绿色生活 施耐德电气围绕软件定义的自动化开放自动化和工业可持续等方面带来
新材料专区“首秀”助推低碳环保发展 进博会看未来绿色生活 施耐德电气围绕软件定义的自动化开放自动化和工业可持续等方面带来 - 我国首次发布国家生态保护修复公报 来源标题:我国首次发布国家生态保护修复公报11月6日,在2024东亚海
- 天津公安强化大数据赋能 基层警务插上智慧翅膀 来源标题:基层警务插上智慧翅膀(法治头条)在天津市河西区,有一支
- 瓜州县:电网改造为乡村注入“电动力” 为改善农村用电环境,优化电网网架结构,增强电网供电能力。今年以
- 10余年间我国实有民营经济主体增长超4倍 来源标题:我国实有民营经济主体增长超4倍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
-
 用爱浇灌未来:聚焦“开心屋”,关注儿童心理健康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心理健康至关重要。2024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
用爱浇灌未来:聚焦“开心屋”,关注儿童心理健康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心理健康至关重要。2024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 - 教师资格考试(面试)11月8日开始报名 来源标题:教师资格考试(面试)明日开始报名近日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发
-
 “我要取土”匹配“我要弃土” 全国首个水土保持土石余方数智平台上线 来源标题:我要取土匹配我要弃土 全国首个水土保持土石余方数智平
“我要取土”匹配“我要弃土” 全国首个水土保持土石余方数智平台上线 来源标题:我要取土匹配我要弃土 全国首个水土保持土石余方数智平 -
 川藏线日记丨昨日、当下、未来在“香格里拉”交相辉映 来源标题:川藏线日记丨昨日、当下、未来在香格里拉交相辉映从川藏
川藏线日记丨昨日、当下、未来在“香格里拉”交相辉映 来源标题:川藏线日记丨昨日、当下、未来在香格里拉交相辉映从川藏 - 0开头的股票是什么股?300开头股票为啥不能买? 0开头的股票是什么股?0开头的股票是深证交易所上市的股票,以000和0
-
 【理响中国】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 来源标题:【理响中国】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 漫话新征程·
【理响中国】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 来源标题:【理响中国】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 漫话新征程· - 错峰游、赏景游、入境游——湖南张家界旅游持续火热 记者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遇到双语导游刘桥时,他正用一口流利的英
-
 央行11月18日发行2025中国乙巳(蛇)年贵金属纪念币一套 据央行网站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024年11月18日发行2025中国乙巳(
央行11月18日发行2025中国乙巳(蛇)年贵金属纪念币一套 据央行网站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024年11月18日发行2025中国乙巳( - “一户一条救助链”,医疗救助对象信息共享机制年底全覆盖 来源标题:一户一条救助链,医疗救助对象信息共享机制年底全覆盖11
- 到2027年末,我国八成二级以上医院将设老年医学科 来源标题:到2027年末,我国八成二级以上医院将设老年医学科11月6日
- (乡村行·看振兴)山西寿阳:下好产业“先手棋” 跑出振兴“加速度” 来源标题:(乡村行·看振兴)山西寿阳:下好产业先手棋 跑出振兴加
-
 出行,未来无限可能——第七届进博会汽车展区前瞻  这里展示出未来出行的N种可能,现场90%的展出车型为新能源车
出行,未来无限可能——第七届进博会汽车展区前瞻  这里展示出未来出行的N种可能,现场90%的展出车型为新能源车 -
 “雨中挡住车流,为伤者撑起一把爱的伞” 他们的善举值得点赞! 近日,在广东阳江街头上演了感人一幕。一把带着善意的雨伞,在雨中
“雨中挡住车流,为伤者撑起一把爱的伞” 他们的善举值得点赞! 近日,在广东阳江街头上演了感人一幕。一把带着善意的雨伞,在雨中 -
 东风猛士科技成为第十五届珠海航展全球合作伙伴 为航展“保驾护航” 大国重器,壮志凌云。2024年11月5日,东风猛士科技与珠海航展集团战
东风猛士科技成为第十五届珠海航展全球合作伙伴 为航展“保驾护航” 大国重器,壮志凌云。2024年11月5日,东风猛士科技与珠海航展集团战 -
 共启合资合作新篇章 一汽-大众与大众汽车集团进博会签署合作备忘录 11月5日,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下简称进博会)在上海开幕。会
共启合资合作新篇章 一汽-大众与大众汽车集团进博会签署合作备忘录 11月5日,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下简称进博会)在上海开幕。会 - 车企争相驶入人形机器人赛道 近日,市场传出赛力斯进军人形机器人赛道的消息,带动A股人形机器人
-
 “行走”的充电桩,能否破解老旧小区汽车充电难? 近年来,我国顺应汽车产业变革趋势,统筹推进技术创新、推广应用和
“行走”的充电桩,能否破解老旧小区汽车充电难? 近年来,我国顺应汽车产业变革趋势,统筹推进技术创新、推广应用和 -
 张兴海:坚持软件定义汽车 问界持续探索“无人区” 11月7日,由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经济参考报社主办的第七届中国企
张兴海:坚持软件定义汽车 问界持续探索“无人区” 11月7日,由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经济参考报社主办的第七届中国企 - 股票期货交易方式有什么特点?期货是股票的一种吗? 股票期货交易方式有什么特点?1、成交和交割的非同步性期货成交时,
- 教育部计划举办40余场招聘活动 提供300余万个就业岗位 来源标题:教育部计划举办40余场招聘活动 提供300余万个就业岗位昨
-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与学支联文旅达成深度战略合作,构建长三角文旅发展大格局 2024年11月6日,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文化和旅游局、嘉兴市南湖区人民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与学支联文旅达成深度战略合作,构建长三角文旅发展大格局 2024年11月6日,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文化和旅游局、嘉兴市南湖区人民 - 镇原县孟坝镇:“我在城里有块田”的文明新实践 近日,走进庆阳市镇原县孟坝社区步行街易地搬迁安置点,阳光透过薄
- 油价年内第9次下调 国际油价短期运行波动性较强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自11月6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
- 国家电网甘肃电力:贴心服务促庆阳光伏并网发电 近日,国家电网甘肃电力(庆阳南梁)连心桥共产党员服务队深入庆阳市
- 肃北县河西片区重点项目竣工投用 近日,肃北县河西片区重点项目竣工投用仪式举行,标志着河西片区重
- 大堡镇:就业工厂进村 助力群众增收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近年来,陇南市康县大堡镇把稳定就业作为做好生
- 孟坝镇:闲置空地变身“绿色共享菜园” 开启文明新篇章 近日,走进庆阳市镇原县孟坝社区步行街易地搬迁安置点,阳光透过薄
热门资讯
-
 用爱浇灌未来:聚焦“开心屋”,关注儿童心理健康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心理健康至关...
用爱浇灌未来:聚焦“开心屋”,关注儿童心理健康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心理健康至关... -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与学支联文旅达成深度战略合作,构建长三角文旅发展大格局 2024年11月6日,浙江省嘉兴市南湖...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与学支联文旅达成深度战略合作,构建长三角文旅发展大格局 2024年11月6日,浙江省嘉兴市南湖... -
 七届“全勤生”高通已经确认参加明年第八届进博会 11月5日至10日,第七届中国...
七届“全勤生”高通已经确认参加明年第八届进博会 11月5日至10日,第七届中国...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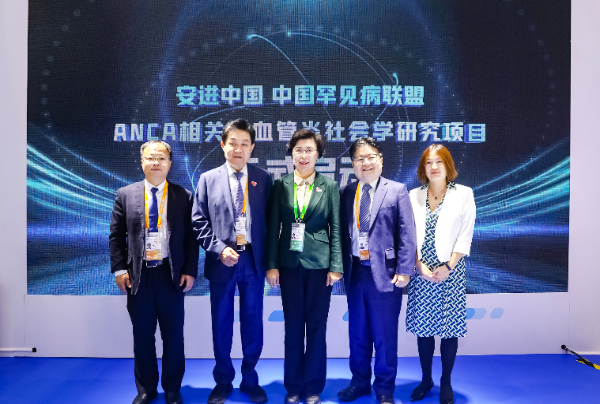 进博故事|进速向新:安进携多款创新疗法闪耀进博 新华网上海11月7日电(逦琛) 第...
进博故事|进速向新:安进携多款创新疗法闪耀进博 新华网上海11月7日电(逦琛) 第...
观察
图片新闻
-
 东风猛士科技成为第十五届珠海航展全球合作伙伴 为航展“保驾护航” 大国重器,壮志凌云。2024年11月5...
东风猛士科技成为第十五届珠海航展全球合作伙伴 为航展“保驾护航” 大国重器,壮志凌云。2024年11月5... -
 温暖贴心 进博会新闻中心举办活动庆祝第二十五个记者节 11月8日,恰逢第二十五个记者节,...
温暖贴心 进博会新闻中心举办活动庆祝第二十五个记者节 11月8日,恰逢第二十五个记者节,... -
 在深谷山野中 感受海南黎族文化   11月4日在位于海南保...
在深谷山野中 感受海南黎族文化   11月4日在位于海南保... -
 部署重点任务 我国加快谋篇布局低空产业   图为11月5日,小游客...
部署重点任务 我国加快谋篇布局低空产业   图为11月5日,小游客...
精彩新闻
- 赵钱坝村:如画美景与产业共兴的乡村新篇 在陕甘川三省交界地带,有一个如诗...
-
 陇南成县:“暖心”活动奏响文明实践“暖冬”曲 理论宣讲、文化演出、书画惠民、健...
陇南成县:“暖心”活动奏响文明实践“暖冬”曲 理论宣讲、文化演出、书画惠民、健... - 镇原县孟坝社区:创新文明实践 打造活力安置点 近日,走进庆阳市镇原县孟坝社区步...
-
 消防演练进校园 安全知识伴成长——驻马店市第二十小学开展消防安全教育系列活动 为进一步加强校园安全工作,深入推...
消防演练进校园 安全知识伴成长——驻马店市第二十小学开展消防安全教育系列活动 为进一步加强校园安全工作,深入推... - 镜头连中外·第69辑 |“小羊驼”来了!秘鲁“温暖驼”连续七年参展进博会 来源标题:镜头连中外·第69辑 |...
- 陕甘川交界的明珠——赵钱坝村的发展之路 在陕甘川三省交界地带,有一个如诗...
- 进出口银行:调研甘肃重点行业 服务地方经济 为更好支持甘肃省绿电、储能等新兴...
- 前三季度江西省规上服务业实现营收3419.5亿元 同比增6.6% 记者近日从省统计局获悉:今年以来...
- 泰国卫生部针灸培训班:在甘肃探寻中医奥秘 历经近一年在泰国的中医理论知识学...
- 凉州区:“专精特新”企业成为经济发展新引擎 武威市凉州区持续加力专精特新培育...
- :传承与创新的敦煌乐章 由甘肃演艺集团耗时近两年打造的《...
- 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再登进博会中国馆 以国礼形象展现中国风采 走进中国馆,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
 林周县秋色宜人 秋景如画 来源标题:林周县秋色宜人 秋景如...
林周县秋色宜人 秋景如画 来源标题:林周县秋色宜人 秋景如... - 兰州大学:为黄河流域研究贡献多支力量 在漫长的历史中,黄河是什么时候开...
- 粤港澳公路自行车赛11月下旬在珠港澳三地举行 本次赛事是由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
- 新疆吐尔尕特口岸降大风雪 中吉双方保通关顺畅 11月6日,受冷空气影响,新疆吐尔...
- :连接敦煌与“冰丝带”的艺术之旅 敦煌,有多少种呈现方式?这次,把...
- 高善穆石造像塔:佛教与道教融合的千年见证 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的国宝级文物高...
- 山东沿黄省级重大项目环评时限压减30%以上 环境影响评价是优化产业布局、完善...
-
 日喀则农牧业特色产业绘就乡村振兴绚丽篇章 来源标题:日喀则农牧业特色产业绘...
日喀则农牧业特色产业绘就乡村振兴绚丽篇章 来源标题:日喀则农牧业特色产业绘... - 2024内蒙古优秀剧目展演月启幕 畅享艺术盛宴 11月6日晚,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 “科技+保险”如何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专家解读→ 来源标题:科技+保险如何为乡村振...
-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药学部主任药师枉前:合理用药守护患者健康 来源标题: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药...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药学部主任药师枉前:合理用药守护患者健康 来源标题: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药... -
 温暖贴心 进博会新闻中心举办活动庆祝第二十五个记者节 11月8日,恰逢第二十五个记者节,...
温暖贴心 进博会新闻中心举办活动庆祝第二十五个记者节 11月8日,恰逢第二十五个记者节,... - 进博故事|进速向新:安进携多款创新疗法闪耀进博 来源标题:进博故事|进速向新:安...
-
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吸引游人 11月7日,四川省广元市,剑门关关...
-
 七届“全勤生”高通已经确认参加明年第八届进博会 11月5日至10日,第七届中国...
七届“全勤生”高通已经确认参加明年第八届进博会 11月5日至10日,第七届中国... - 技术装备展区吸引观众 11月7日,第七届进博会技术装备展...
-
 兜底线、惠民生 落实医疗救助制度 让困难群众有“医”靠 国家医保局、民政部11月7日发出通...
兜底线、惠民生 落实医疗救助制度 让困难群众有“医”靠 国家医保局、民政部11月7日发出通... - 甘南迭部:篮球赛事开启冬季旅游新篇章 11月5日至12日,五省(区)高原地区...
- 多连杆和麦弗逊悬挂哪个好?多连杆一般是几连杆? 多连杆和麦弗逊悬挂哪个好?一、麦...
- 中医魅力:吸引泰国西医的跨国学习热潮 历经近一年在泰国的中医理论知识学...
- 黑色车漆被划伤露白底如何修复?黑色车漆失去光泽的原因有哪些? 黑色车漆被划伤露白底如何修复?对...
-
 国际赛事落地京山 助力软式网球运动跃上新台阶 2024年第四届世界青少年软式网球锦...
国际赛事落地京山 助力软式网球运动跃上新台阶 2024年第四届世界青少年软式网球锦... -
 高通中国区董事长孟樸:与产业紧密合作共拓全球市场 骁龙®8至尊版移动平台、名爵 ...
高通中国区董事长孟樸:与产业紧密合作共拓全球市场 骁龙®8至尊版移动平台、名爵 ... -
 第十六届世界美发大会厦门启幕 荟萃世界美发艺术 第十六届太空之旅世界美发大会7日...
第十六届世界美发大会厦门启幕 荟萃世界美发艺术 第十六届太空之旅世界美发大会7日... - 中国经济增长之“内功”必破美国打压遏制之“暗箭” 来源标题:中国经济增长之内功必破...
- 手动档车如何打火?手动档车变速箱齿轮油多少时间换一次? 手动档车如何打火?1、在启动之前,...
- 嘉宾话进博丨伊朗工矿贸易部副部长:进博会展现中国经济规划的长远性 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伊朗国家...
- 2025年军队文职人员公开招考工作全面展开 为广泛延揽社会优秀人才服务军队建...
- 超强台风“银杏”迫近 海南发布海上大风四级预警 来源标题:超强台风银杏迫近 海南...
- 海南优化新生儿出生“一件事”服务 改善群众就医体验 海南省通过优化新生儿出生一件事服...
-
 “镜中行旅”主题展览亮相上海当代艺术馆 上海当代艺术馆镜中行旅主题展览,...
“镜中行旅”主题展览亮相上海当代艺术馆 上海当代艺术馆镜中行旅主题展览,... -
 央视快评丨为促进文明传承发展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作出更大贡献 来源标题:央视快评丨为促进文明传...
央视快评丨为促进文明传承发展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作出更大贡献 来源标题:央视快评丨为促进文明传... - 川渝共建世界级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取得新进展 来源标题:川渝共建世界级装备制造...
-
 星空有约|公历11月与农历十月的日期完美重合 来源标题:星空有约|公历11月与农...
星空有约|公历11月与农历十月的日期完美重合 来源标题:星空有约|公历11月与农... -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江西已建成近1.2万家就业之家 来源标题: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江...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江西已建成近1.2万家就业之家 来源标题: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江... -
 天津北大港湿地白枕鹤种群刷新观测记录 来源标题:天津北大港湿地白枕鹤种...
天津北大港湿地白枕鹤种群刷新观测记录 来源标题:天津北大港湿地白枕鹤种... - 40余场专场招聘将启动!“秋季校园招聘月”来了 日前,教育部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
-
河南郑州:“种业创新引领成果展”展示农业“芯”成就 11月7日,2024中原农谷国际种业大...